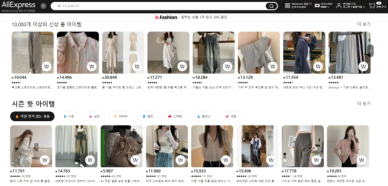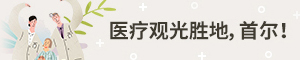于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幸好基督教足够宽容。想一想也是,世上批评基督教的声音不绝于耳,却很少听说有基督徒站出来恶声恶语地反击,更别提像其他团体一样动不动就全球追杀,或动不动就包围报社及政府机构了。
老舍《正红旗下》未完成
提起教堂,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至少应该高大巍峨,或者古色古香。这可能与天主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有关。在北京,有若干天主堂,如南堂、北堂和东堂,不管是哥特风格尖顶入云,还是巴洛克风格雍容华丽,外墙的雕花、内堂的穹顶以及玻璃窗的彩绘总是那么炫人眼目。
基督堂则大多朴素。据我了解,朴素非因缺钱,他们只是更愿意把钱花到紧要处,如帮助穷苦人,或赈灾救难。北京另一座有历史的基督教会亚斯立堂,还稍具西洋风格;缸瓦市堂则朴素一如北京古老的四合院,让人很难想到,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会,创立于1863年。

关于缸瓦市堂的初创,有三个外国人的名字值得记住。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受基督教伦敦会委派,1861年来到北京,在东城租住英国公使馆的房屋,创办医疗事工,即边行医边传教。基督教早期流行有这样的特点,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教会大多与医院结为一体,先医治人们身体的病痛;然后,当灵魂遭遇困境时,人们就更容易相信福音。雒魏林的医疗事工,是协和医院的前身。
1863年,伦敦会又派来一位艾约瑟,与雒魏林共同负责传教工作。他们在西城正式设立传教机构,这就是缸瓦市堂的前身。到1864年,医学博士杜德珍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行医的同时传教,为缸瓦市堂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作家老舍则是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1921年,少年老舍在缸瓦市堂读夜校学英语,兼做杂役,1922年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老舍以小说《骆驼祥子》知名,还有《四世同堂》传世,但评论一向认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未及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这里的“红旗”,与歌者崔健《红旗下的蛋》里的“红旗”不同,指的是满洲八旗之一。老舍的父亲是低级军士,隶属正红旗。正红旗第一代旗主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后来接任汗位,代善这一支派就逐渐衰微了。因此,正红旗在满洲八旗中人口最少,属下五旗之一,穷苦人居多。
在《正红旗下》中,老舍对贫寒的家境有催人泪下的描写,但对于在缸瓦市学习及受洗这一重要经历,却丝毫没有着墨。反而,还塑造了一个反面角色牛牧师。我不认为他这样写是出于真心,我更相信他是不得不迎合时势。要知道,在1958年,北京西城各教派教堂就全部关闭了,通通合并到了缸瓦市堂。老舍不可能不感觉到这种压力。
如实写自己对教会的感情,政治上极度危险。按当时流行的口径编造牛牧师有多坏,他心里也难免刺痛感。很可能正是这种内心的冲突,让老舍的《正红旗下》只写了8万字就断然搁笔了。在那样一个严酷的时代,《正红旗下》是注定无法完成的作品。要知道,当时,老舍为了与新政权和谐相处,姿态已经相当低了,连相声、大鼓书和快板书都肯写。可最后,新政权还是没有给他留出起码的生存空间。在遭遇一顿屈辱的毒打之后,老舍自沉太平湖。退一万步讲,尽管此举有违基督徒伦理,但在我看来,未尝不是一种自洁的选择,否则,就可能不得不像郭沫若一样作诗高呼“斯大林是我亲爷爷”——这种灵魂的自戕,要比肉体死亡更让人痛心和战栗。
心有所属,爱有所属
缸瓦市堂坐落于北京西城西四南大街,一主堂,一副堂,一小堂。主堂屋顶高高的十字架十分抢眼,经常可以见到路上的行人好奇地向大门里张望。在我接触基督教前,也曾是那些探头探脑的人之一。依我们所领受的日常教育,非常容易对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机构和宗教人士抱有深深的戒心,因此,今天还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人和当年的我一样,并不知道,走进教堂的大门,就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即使你不会马上皈依,但只要你靠近,照样可以体验到那种圣洁与光辉所带来的安全与宁静。

所以,站在缸瓦市堂并不宽敞的院落里,我想的是,如果能在门口立一块牌子就好了,上面可以这样写:“随时欢迎您走进来,哪怕只有一杯清水的缘分,我们也视为珍贵。”就是说,教堂可以为路人提供清洁的饮水,让所有好奇的人都放心地走进来,不用对他们宣教,只让他们知道,这里一点都不神秘,这里只是清凉的绿荫——这可能为未来埋下无数向善向上的种子。
1863年的教堂是什么样,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它毁于1900年义和团的大火。缸瓦市堂1903年重建,当时分为南北两院,有大小礼拜堂,有仁济医院,有铭贤小学。教会办医疗,办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但到1966年,北京所有教堂都停止了活动。这一时期,宗教人士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对此完全缺乏了解。当那些被迫赋闲的牧者在无月之夜仰望星空时,哪一只眼睛率先蓄满了泪水?可以说,在信仰的问题上,基督徒无比谦卑,自认罪人,自认软弱,因此,才需要信仰的日日浇灌与支撑。而信仰一旦被禁止,就相当于试图禁止我们的软弱,可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像螺丝钉一样刚硬。
夜幕降临,缸瓦市堂屋顶的十字架亮起来了。于是就想,什么时候,北京也能像首尔一样,在任何一座楼顶望出去,满眼都是十字架的红光。对于教会,韩国国内舆论也有“公司化”的批评,但我知道,相比之下,教会对社会的良性影响,才是更值得大大彰扬的。我们都承认,没有哪一种宗教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一切恶人都改造为良人,但至少,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好人可以找到自己的队伍,并在其中获得坚持行善的源源动力,有敬畏,知行止,与权力客气,与恶行隔绝。

我一直相信,道德成长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我们学知识,学技能,设学校,交学费,从来不吝于投资。可是,事关重大的道德问题,我们的社会与个人却几乎没有投入,任由动物性自然生长。可以说,在欧美,在韩日,教会都是专业的道德养成机构,政府给予免税待遇,个人为教会诚意捐输,实际上都是在进行道德投资。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没有投入,怎么可能指望社会具有及格以上的道德水准?像吃饱了不饿一样,这是世间最为简单的道理。
当然,我也知道,以上想法,明显过于功利,真正的基督徒并不这样想。但是,他们也不会为此与我强辩,他们只凝望,只默祷,心有所属,爱有所属,把一切感动与热诚,都交付自身与上帝的交通之中。
文/王元涛
图片说明
001:朴素的缸瓦市堂
002:主堂讲台
003:从副堂看唱诗班
004:爬满绿藤的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