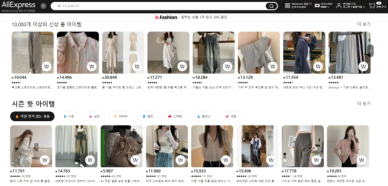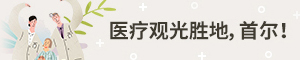“悲情城市的女人”朱天文近日代表台湾地区参加由韩国浦项制铁公司青岩财团举办的“亚洲文学论坛”。《悲情城市》是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拍摄的电影,1989年在威尼斯电影节得到大奖--圣马可金狮奖。这部电影是韩国影迷也十分熟悉的。

宛如一场悲剧,又像藤蔓纠结般的台湾现代史先后经过西班牙、荷兰以及日本的殖民统治,“迎来”的却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侯孝贤导演以光复后二·二八事件和台独运动等惨痛历史为主体,将历史的暴力直接融入一个家庭的命运中,用独特的拍摄技法完成了极具象征性的画面语言。《悲情城市》可谓是“用电影撰写的历史”,该电影剧本作家就是朱天文。
包括《悲情城市》在内,让小镇九份一举成为旅游胜地的电影《恋恋风尘》、《虚梦人生》及《好男好女》剧本都是朱天文写的,通过剧本深层切入到侯孝贤的作品世界。因此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她文学天赋,没有她积累的文学才华,侯孝贤的电影也许无法如此成功。朱天文的文学是将“电影和小说”当作轨道的巨大火车。
朱天文出生于1956年,毕业于台北中山女高和淡江大学英文系。从16岁开始踏入文坛的朱天文已经有40余年的文学经历。少女时期受到张爱玲的丈夫、也是苦命文学家胡兰成的影响,就运营名为“三三集刊”的文学沙龙。当时,她是深受大家期待的文坛天才。
她同时以宏观和微观的视觉观察和描写战后台湾的社会、特殊情况以及女人的生涯。她的文学省察通过《淡江记》、《传说》、《最想念的季节》等小说集体现清洗的脉络走向,到《世纪末的华丽》建立里程碑,以《荒人手记》和《花忆前身》等作品持续深入下去。
《亚洲周刊》将她的《世纪末的华丽》选为“20世纪中国百大小说”之一,笔者为何把该作品当成她文学生涯的里程碑?因为该作品如实记录着这样一个时代:几乎维持了40年的戒严终于开解,冷战时代最终结束,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解体,朱天文对自己此前的文学基础—“现代性洗礼”发出质疑,并成功实现解构与超越。
台湾的现代历史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
台湾与韩国一样是世界最后被人为分割的地区,仍然饱受着隔绝、离散(Diaspora)的痛苦,并被两岸问题折磨着,而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长时间的军政府独裁,也经历了这种情况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性的洗礼,并将工业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离乡与农村经济崩溃当作牺牲,最终实现成长了。
就像韩国政治中存在着岭南地区和湖南地区之间的纠葛一样,台湾也有原住民、本省人以及包括“眷村”的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朱天文的文学和电影就是对台湾近代历史的肖像刻画,同时是“美学性开拓”。
尤其是,今年将由“图书出版亚细亚”出版的韩文版《荒人手记》如实地反映她的美学性开拓。从作品的风格和叙事技法到概括为两性问题的情欲和同性恋的主题,可谓饱含世纪末符号的该作品其实不是针对读者而是对作家自己的坦白,也是“单性生殖的狂想曲”。
就像台湾的一位评论家所说的“写作成了最华丽的浪费,最抵死而又空虚的自慰”这句一样,朱天文通过写作确认自我存在。
“我为我自己,我得写。用写,顶住遗忘。我写,故我存在。”
这句话是朱天文通过文学的自我确认,她所发挥的世纪末美学。换句话说,她是在用全身“书写台湾”。
* 本专栏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与本报立场无关。